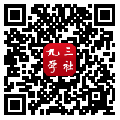1981年,邓稼先院长在四川省梓潼县九院参加党的基本知识考试。
许进的祖父许德珩,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九三学社的卓越领导者和开拓者;他的祖母劳君展,参与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并为九三学社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姑父邓稼先,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为祖国奉献出一生的“两弹元勋”。
随着盛夏临近,追忆邓稼先光辉一生再度掀起热潮。今年6月25日,是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奠基者之一、“两弹元勋”邓稼先诞辰90周年。
纪念日前夕,全国政协委员许进讲述了他的姑父邓稼先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壮丽人生
“初春的圆明园。芳草萋萋,春意阑珊。大水法的石堆前,两个5、6岁的男孩在玩耍。一个叫杨振宁的孩子偶尔发现了一枚子弹,他拿给小伙伴邓稼先看,他们判断,这一定是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时留下的。握着这颗子弹,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长大后要造一枚最厉害的子弹,看谁还敢欺负中国……”
这是不久前,清华大学演出的念邓稼先的话剧《马兰花开》开场的一幕。

1984年10月16日邓稼先与聂荣臻、张爱萍庆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二十周年。
1953年,美国政府为了挽救败局、尽早结束朝鲜战争,曾企图向我志愿军和东北地区投放原子弹。通过这场战争,中国领导人更充分地认识到了先进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1955年初,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研制原子弹。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术秘书、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兼第二机械工业部(即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教授推荐他的助手,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邓稼先到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即核武器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主持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从此,邓稼先带领几十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祖国的尖端国防事业当中。1962年,中国的原子弹理论方案诞生;1963年,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完成;1964年,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底,氢弹的理论设计完成;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人用了八年六个月,美国人用了七年四个月,英国人用了四年七个月,苏联人用了四年。而中国的科学家仅用了两年八个月!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年轻的共和国创造了奇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颗耀眼的太阳出现在中国的西部,一朵美丽的蘑菇云腾空升起。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成功地在西部大沙漠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核大国对中国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几天前,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飞机把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和邓稼先等科学家接到罗布泊试验场,观看试验。望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刚满四十岁的邓稼先不禁热泪盈眶。
“他也许是为祖国的日益强盛而流泪,也许是为自己给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流泪,也许是为自己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而流泪。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的今天,国人可能难以体会四十多年前的这一天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是多么重要,对于提升民族的地位是多么重要,对于西方世界的震撼是多么强烈。在祖国的经济和技术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的科学家们用他们的智慧制造出了两弹一星,用他们的脊梁把年轻的共和国托起到与核大国平起平坐的谈判桌上。”
邓稼先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战略家。1985年8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并立即进行了手术。邓稼先忍着手术和化疗带来的痛苦,用他的睿智和微弱的生命在病床上写出了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规划的建议书。建议书很快就被党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十年后,我国的核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人格魅力
邓稼先能够成功地率领理论组在八年内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除了敏锐的物理直觉和非凡的数学思维之外,还与他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远见卓识、不计名利、身先士卒是邓稼先的优秀品质,也是他的团队能够取胜的关键。
“杨振宁博士把钱三强教授推荐邓稼先主持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与葛若夫斯选聘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相提并论,他说,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理论部组建时,在当时的国力下研制原子弹,科学家们面临着难以形容的困难。理论部里面学习核物理专业的仅邓稼先一人,甚至刚刚组建的九院也只是一片高粱地。这些困难被邓稼先的团队一一克服了。白天,邓稼先带领这些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砍高粱、挑土、平地、修路、砌墙、抹灰,自己动手修建实验室和办公室。晚上,他给大家讲他在美国学到的核物理知识。那时,苏联政府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并派了一些专家来中国,这使邓稼先感到一点安慰,他虚心地向苏联专家学艺。谁知不久后中苏关系破裂,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撤走了专家,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苏联专家在临走前对邓稼先他们说:“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

邓稼先在打乒乓球
“邓稼先利用他的知识和智慧选择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课题为理论组的主攻方向。事实证明,邓稼先正确地选择了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为我国早日完成原子弹的总体设计方案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始设计原子弹理论模型时,没有电子计算机,他们就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计算数据。他们把用过的草稿纸扎成捆,放进麻袋里保存起来。日积月累,这些麻袋从地面摞至天花板,最后竟堆满了一个房间。邓稼先与他的同事们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原子弹的总体设计方案,在这四年中他们读了多少书,列了多少方程式,作了多少次演算是后人和局外人无法得知的。在九院的保密室里保存着邓稼先100多本笔记本。这100多本笔记本蕴含着多少他的心血啊!他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二十多年,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探索性研究工作都是他亲手把关,最后拍板的,很多方案都是他亲笔写就的,而他总是把功劳记在集体的名下。工作时严肃认真的理论组长,休息时变成了孩子王。同事们可以翻邓稼先的兜找好烟抽,可以翻他的抽屉找糖果和饼干吃。他还与同事们玩“跳马”游戏活跃气氛。他弓着身子当马,让青年人从他身上一一跳过……”
翁婿情深
许进是许家第三代传人。他的祖父许德珩,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九三学社的卓越领导者和开拓者;他的祖母劳君展,参与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并为九三学社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姑父邓稼先,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为祖国奉献出一生的“两弹元勋”。
“抛开已经熟为人知的英雄事迹,我更想记叙邓稼先平凡的生活。英雄人物亦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但是为了祖国,他们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1929年,五岁的邓稼先进入北平武定侯胡同小学读书。9.18事变后,日本鬼子强迫中国百姓向日本兵行鞠躬礼。看到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此横行霸道,少年的邓稼先感到十分屈辱和气愤,他宁愿绕道多走路也不向侵略者敬礼。每当日本鬼子占领一座中国城市,他们就强迫各地的中国人举着日本旗游行庆祝。1940年初,北平崇德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邓稼先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了,他气愤地撕碎了日本旗并踩在脚下。事后,邓稼先被迫到四川投靠四叔。临行前,望着即将远行的孩子们,病中的父亲邓以蛰百感交集地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16岁的邓稼先带着父亲的沉重嘱托,母亲和姐姐的伤别眼泪被迫离开家,他怀着救国的理想和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踏上了追求科学之路。邓稼先辗转来到到四川江津,终于重新进入高中读书。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进入物理系学习。1945年8月,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并于次年回到离别数年北平,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
“邓家与许家是世交。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与我的祖父同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是好友。在祖父的记忆中,那时的邓稼先是个顽皮的孩子。祖父与祖母劳君展到邓家做客时,邓稼先一边双手抓着门框用身体荡秋千,一边向父母亲通报来客人了。”
“1950年8月,邓稼先在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即返回祖国。1951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邓稼先加入了九三学社。当时,祖父担任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主席,他们成为了同志。1953年,邓稼先与我姑姑许鹿希(许德珩之女)结婚,他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员。祖父和祖母当面称呼他‘稼先’,两人私下谈话时称呼他为‘邓孩子’,视同己出。”

1963年10月20日,许德珩与婿邓稼先及孙辈在香山公园,中间为许进。
1968年,许进的表姐邓志典(邓稼先之女)与他的姐姐一起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他仍然记得那天姑父替典典背着行李,坐公共汽车到火车站去送她去内蒙的情形。接触过姑父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爱笑的人,可是在那个时候,许进姑姑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天津茶淀农场劳动,表姐远走内蒙古荒漠,妻离子散,他还要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赶在法国人之前研制出氢弹,怎么能笑得出来呢?
“与邓家结为亲家之后,许德珩常到西郊燕园的北京大学朗润园去看邓以蛰。邓教授喜欢喝酒。祖父当时享受食品特殊供应待遇,可以买到茅台酒。祖父去看亲家时经常带上茅台酒。姑姑回家时,祖父问她,我送的茅台酒典典的爷爷喝了没有?姑姑说,他舍不得喝,我们回去时他们父子两人一起喝。祖父听到后开心地笑了。”
在三年灾害期间,有很多人饿死了,更多人因饥饿而浮肿。邓稼先领导的理论组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青年技术人员每天忍着饥饿坚持工作。1960年春节,大家一起包饺子过年,理论组几十人,只有一斤白菜一斤肉,一斤面。大家不让南方来的同事包,生怕他们不熟悉包饺子,把宝贵的菜和肉煮到汤里面。
“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也提到,那时我祖父、祖母,姑父的父亲、母亲把节省下来的粮票支援邓稼先;我姑姑省吃俭用,给邓稼先买饼干;邓稼先把饼干和粮票分给大家的故事。其实,这一点点粮票、饼干,对于那几十位刚刚毕业不久且工作劳累的青年大学生来说,真是九牛一毛,画饼充饥呀!但是,邓稼先这种以身作则,关心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大家,鼓舞着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胜困难。有一次进行模型计算时,邓稼先睡不着觉,他凌晨三点来到机房检查计算结果。天亮了,邓稼先从兜里拿出几斤粮票,分给在场的同事每人四两。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回想起来,同事们依然十分激动,‘拿着老邓给我这四两粮票的感觉,今天你给我四两黄金也无法相比!’当时,没人每月都只有28斤粮票。”
“在参加会议时,祖父经常遇到聂荣臻、张爱萍和钱三强等同志,尽管彼此之间熟悉,但是他们见面时从来没有谈起过邓稼先。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介绍,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祖父的老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严济慈公公曾经对我祖父说邓稼先了不起。祖父另外一次了解姑爹的工作情况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三学社的一次会议上,王淦昌王老走过来对我祖父说:“许老,稼先的工作很有成绩啊!”祖父听后十分高兴。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生前曾经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在核武器研制过程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姑父尊称他为王老师。”
许进还谈起了邓稼先生前的生活情况。“起初,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给姑父一套两居室的楼房。后来,给他调到一套三居室居住,直到他去世。他家里没有沙发,家具也十分简单,除了书架、桌子和床以外没有什么摆设。去世之前一年,姑父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副部长级。他本有资格搬到部长公寓去住,但是他没有搬。姑姑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里面。现在还在用的,唯一的两个单人沙发是1971年接待回国探亲的杨振宁博士时从单位借的。”
“姑姑曾经对杨振宁教授说,中国研究核武器的开支比其他国家少很多。杨先生听后摇了摇头说:若算上科学家的生命,计算结果就不是这样了。的确,在国家经济和技术基础十分薄弱、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掌握“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中国的科学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
领悟先贤
许进深知,作为许家的血脉,作为九三学社创始人的后裔,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脉传承,更不能是落后的一代,有责任把九三学社的历史、传统和精神告诉新成员,使之代代相传,并要超越前辈,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为了这份责任,他不遗余力地奔走着。
许进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并非专职的社务干部,日常工作也非常繁忙。但是多年来,他投入在社务活动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出了本职工作。仅仅2010年至2014年,许进参加九三学社的各类会议和活动就达到150余次。发表文章相关文章30余篇。其中有:《周恩来助许德珩巧断章士钊案》、《小忆祖父许德珩》、《怀念李毅》、《析九三学社的传统》、《用一生践行五四精神——忆祖父许德珩》、《历史的讲台》、《做民主科学精神的继承人》、《五四精神与九三学社》、《祖父许德珩与姑爹邓稼先》、《同根同源 血脉相承》、《先贤光辉 泽被后世》、《和衷共济 再创辉煌》、《辛亥革命洪流中的九三学社先贤》、《肝胆相照 一片热忱》、《毛主席“掐了”劳君展给他买的火腿》、《以史为鉴 创造时代》、《天下为公 振兴中华》、《许德珩夫妇挤钱“聚餐”的往事》、《送别启功先生》、《祖父许德珩数十年的心愿》……

2011年清明节,许进(右)与表哥、邓稼先之子邓志平在中华世纪坛邓稼先塑像前
邓稼先等九三学社先贤的无私奉献精神一直萦绕心中,许进与九三学社有着深厚渊源和情感。自儿时起,他经常听祖父、祖母讲述他们的经历,使他对于九三学社的历史和宗旨有所认识和了解。他还有幸谒见过许多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早期成员,他们都是某个专业的大家,他们的造诣令许进仰慕不已。在他心目中,九三学社就是由这些大学者组成的民主党派。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和社北京市委领导布置的任务,许进都不折不扣地圆满完成。他还利用空暇整理社史资料,从2000年起,在九三学社中央的支持下,用了3年时间收集近两千幅图片,撰写10万余字,编纂《百年风云——许德珩》一书,2003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许进热心社务,积极参政议政。任政协委员期间,他提交了大量提案、信息。如:《关于改进立交桥限高防护设施的提案》、《促进北京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关于开发西城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建议》、《发展食文化 照亮金融街》、《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代表人士研究》、《关于全面检查西城区道路交叉路口交通划线合理性的建议》、《细化管理 节源增效——对于供暖管理的两点建议》、《加强对于违反机动车牌照管理车辆的处罚力度》、《关于“民主科学座谈会”的资料》、《分户计量 有待思量》、《科学地发展和利用绿色能源》、《建设世界城市要靠科技和文化》……2014年全国政协大会期间,他提议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获得99位委员的联署,成为两会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历史、现实和未来,昨天、今天和明天,可以看出,他的视野、他的思考、他的眼界。“面对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我们应当用一份宁静、一份虔诚领悟先人的智慧,使九三学社的民主科学精神穿越时空,代代相传。”(戴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