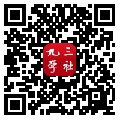五四运动伊始,日方并没有过多关注,认为五四运动并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采取了相对沉默的态度。然而随着运动发展,日本不得不重新认识这场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并采取了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等策略。但新的策略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国内反日运动依然如火如荼。五四运动告一段落后,原敬内阁开始采取了对北洋政府又打又拉的策略,利用亲日政府镇压反日运动。
“一战”期间,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日民族情绪,激化了同美国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日本国内民本主义运动的兴起。1918年爆发的“米骚动”导致了寺内内阁的垮台。当此之时,新一届原敬内阁试图调整对内对外政策。
1918年,原敬内阁指责西原借款招致各国猜疑,决定停止“此类以实业贷款为名,而钻四国借款团章程的空子”的政治贷款。11月11日,外务省召开了讨论对华贷款问题的首脑会议,新任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提出四条改善方案:(1)“放弃过去之侵略主义,凡事以公正态度”对待中国;(2)不采取无视在华外人的权利或损害其感情之政策;(3)鉴于过去对华政策不统一,统一对华外交机构;(4)克服国内对华舆论的分歧。会议同意按这个方向努力。
日本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决心和能力
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政府初始采取了相对沉默的态度。日本政府之所以采取相对沉默的态度,一方面与对华政策的调整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基于对于中国国内局势较为乐观的判断有关。日本之所以对局势作出较为乐观的判断,原因有二:日本认为排斥日货起因于英美及一部分新闻记者、学生团体的煽动,中国商人则“对排斥日货完全不表赞同”,故而“外间排日声浪虽然甚大”,“排斥日货尚未实行,仅止于煽动行为而已。”亲日的北洋政府没有对学生运动采取镇压的态度,对北洋政府施压只能对英美及亲英美政治势力有利。
直到5月16日,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还乐观地估计“当地可能在一、二星期至三星期间完全归于平静,但当地之余波可能渐次波及内地,因此当地之交易在两个月左右期间内不免受到打击,今后三、四个月之夏季期间亦将成为淡季”,但“整个对华贸易上万不至发生足以忧虑之打击也。”有吉不赞成假借官方力量对胁迫排日的煽动行为加以镇压,认为“但目前如由官宪加以干涉,则将使彼等误解排日行动已经收效,日本人已因痛苦不堪而依赖官宪;排斥日货之举以后将成为抵制日本人之唯一武器,实事以排斥日货对待矣。”他主张“无论彼等以任何排日手段,我应采取丝毫不感觉痛痒之态度,暂时旁观,任其所为。”日本民间也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决心和能力。
面对运动的发展,日本政府的态度开始渐趋强硬。5月18日,日本公使小幡就北京学生团体反对日本人的行动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20日,日使再次提出抗议,其中注重之点,仍在学生开会及演说,抵制日货、侮辱日人等事。同时指摘芜湖、南京、杭州等处学商各界,抵制日货之举动为暴烈。由于国民政府并未当即作出切实回答,日使表示将再提抗议要求国民政府采取行动。第二天晚间,日本公使以正式公文致中华民国外交部,又一次提出交涉。日使在照会中对林长民所著《外交问题警告国人》一文中的言论提出抗议,照会中说“为照会事:照得前有巴黎山东问题决定之报,外交委员会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众誓死图之’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皆本使之深以为憾者。”照会并对5月19日《国民公报》所载,北京民国大学生外交救济会启事提出交涉。日方认为,该启事是“以倭奴之为中国患久矣”为前提,照会指摘云:“此项言动,全然接口国民自决,或补助政府等词,鼓吹无政府主义。故意馋诬友邦国家国民。而即是全然敌国视者矣。贵国政府对此行动,毫无取缔,宁是不可解也。”照会威胁说:“若果放置此风潮,不特有酿成贵国内治意外之扰乱,怕有惹起两国国际重大之事态。”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妥为办理。”
在日方压力下,北洋政府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20日,国务总理钱能训与警察总监吴炳湘及步军统领李长泰商议取缔学生运动。孰料吴李均认为学生演说及抵制日货并没有扰乱治安,因而政府无权干涉。21日,徐世昌下令,任命有“屠夫”之称的王怀庆任步军统领,替换了镇压学生运动不力的李长泰。自23日晚上起派右四区署员对“奖励学生运动”的《晨报》、《国民公报》的发稿进行检察。24日将“煽惑军队,鼓荡风潮”的《益世报》封禁,并将编辑潘蕴巢等拘留。《五七日报》和《救国周刊》也因力倡争青岛问题,被指“扰乱治安”,印刷局被封,政府派警察在各处禁止发买。5月22日,内务部发出严禁学生干预政治以及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训令。5月23日,内务部又发出镇压北京反日运动的训令。要求京师警察厅“密行查察,分别依法办理。”23日和28日,内务部接连电告各省区,唯恐反日运动“激起事端,招友邦之责言,贻国家以巨患”,要求各地“标本兼治,弭患无形。”25日,大总统下令京外文武长官禁止学生进行反帝爱国活动,要求地方长官“剀切晓谕,严密稽查,如再有前项情事,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同一天,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限3日内结束罢课,一律复课。北京政府的威压并没能使爱国学生屈服。5月26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所属的36所学校一致主张把斗争进行到底。5月28日,即限令复课期满之日,学生们没有遵命复课。
五四运动给日本商业以沉重打击,《大阪每日新闻》说:自上月抵制风潮发生以来,日货输出大为减少,计五月份之输出额,较之平时已减去百分之三十。大阪所受影响尤为特甚,本市川口地方有华人商店专办日货者,为大势所迫不得不闭门停业焉。
6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接连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是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进行辩护,另一道命令是再次要求取缔爱国运动,并要求学生立即复课。爱国学生无比愤怒,决定自3日起,恢复街头讲演。3日,北京各校学生陆续上街演讲。警方根据徐世昌5月25日命令,逮捕了170余人。次日,警方出动马队冲撞学生并逮捕了700余人。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学生纷纷罢课,并分头动员工界罢工,商界罢市。5日,上海的部分工厂、商店举行罢工罢市。五四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把上海的这次斗争和由此掀起的全国斗争称作六三运动。在上海燃起的“三罢”斗争烈火,迅速燃遍各地。
5月下旬,此时日本已处于对华面临进退两难的处境。从日本长远利益考虑,要暂时缓解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以利将来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和控制。但相对温和政策势必会影响日本眼下的利益。故而日本在这一阶段有些举棋不定。6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曾指示:“对于现时之风潮,不可强求中国政府予以取缔……亦应避免贸然对中国官民施加压迫及挑拨反感之举;须冷静观察事态,对中国官宪经常保持良好关系。”六三运动爆发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日本舆论开始批评政府对华政策,鼓吹日本政府对北洋政府施压。6月12日,东京《时事新报》发文称“现在外国工部局与中国官宪,虽极力镇抚,然租界内外之险象,不特丝毫未尝减轻,且日增月盛,此处若不及时扑灭,则各地必闻风效尤,贻中外官吏之隐忧犹大。故为中外官吏计,诚宜及今以高压手段扑灭之为宜,而为外国计,及今各令其军舰之将卒上陆,尤为上策。”16日,《大阪每日新闻》发文要求原敬内阁反思,调整对华政策,认为“若必追随列国之后,仍标榜不干涉,使内乱坐大,此原内阁不得不郑重考虑者也。”日本的眼前利益受到巨大威胁,内田的指示无法得到实施,日本转而开始重点维护既得利益。
新形势迫使日本采取新的对华政策
日本政府采取对北洋政府进一步施压和拉列强下水的策略。除了对北洋政府外交施压、武力恫吓外,还煽动列强。6月6日在五国使团会议上,日本公使小幡别有用心地说:“中国人民受政治之煽惑,借抵制外货之名,吾等旅华外人颇受危险,深恐酿成庚子之祸” ,怂恿英、美共同镇压运动,企图将列强绑在同一辆战车上。美国人不为所动,因为他们看出“这个运动是单只反对日本的,幸而与我们无关,已没有排外的意思。”由于五四运动并不是针对欧美列强,从总体上看,欧美列强方面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基本采取旁观的态度。
六三运动发生后,各地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不可遏止。焦头烂额的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下令将曹、陆、章三人罢免。6月11日徐世昌向国会提出辞职,6月13日钱能训内阁垮台,北洋政府自顾不暇,一时无力按日方要求对群众运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6月26日,小幡至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北洋政府对“无保留签字”予以明确答复,被中方拒绝。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和约签字。五四运动告一段落。但中国各地民众继续抵制日货。1919年7月初上海关日货入口与1918年同期相比大为减少,具体情况如下表:
面对此种局势,原敬内阁对北洋政府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方针。9月9日,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拉拢亲日派,决定提供借款,接着就再三向北京政府施压,要求取缔排日活动。原敬内阁成立之初,借批判“西原借款”而声称要改变的对华政策,至此大大后退了一步。
总的说来,五四运动中日本对华策略未能实现其目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坚定的斗争。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表现出的爱国热情,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都是值得永远铭记的。
编后: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著十分丰富,但对于五四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日本对五四运动的反应,目前尚缺少专门的论述。面对当时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日本的对华政策有何改变,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日本的对华政策达到既定目标与否等都值得去探讨。本文试图就日本对五四运动后对华政策的改变及其效果展开论述,角度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