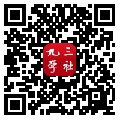黎锦熙(1890一1978) 字劭西,湖南湘潭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慧眼识巨才
1913年,黎锦熙因不屑与官宦为伍,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满怀大志又手头拮据的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次年春,他们又随着四师与一师合并一起转到一师。当时黎锦熙讲授历史课,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课程。这个身材瘦高、聪慧睿智且温文尔雅的学生很快就引起黎锦熙的注意,并很快成为挚友、兄弟。黎锦熙学贯古今,学识渊博,而且品行笃正,堪为人师。因此,毛泽东经常到黎锦熙住处请教,问题涉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特别是关于如何治学等问题。黎锦熙总是循循善诱耐心教导。毛泽东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闻黎君劭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密焉,人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之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黎锦熙对毛泽东评价非常高,在1915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俩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这是黎锦熙慧眼识巨才以及作为一位教师对培养青年毛泽东的强烈责任感。
黎锦熙在生活上也时时处处关心毛泽东,他知道这个农村青年求学不易;他与杨昌济、徐特立等人曾创办《湖南公报》《公言》等刊物,宣传民治思想。黎锦熙常请毛泽东等学生帮助抄写稿件,给一定的酬劳。几十年后,黎锦熙曾欣慰地说过:在湖南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帮助抄写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即田汉同志;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其实就是毛泽东,是黎锦熙没有明说罢了。
1915年9月,黎锦熙赴北京任职,使这对挚友被迫分离。到1920年,毛泽东曾六次给黎锦熙写信,称黎锦熙"弘通广大","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挚友。黎锦熙则"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给予极高评价。1918一1919年毛泽东因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和驱逐张敬尧事曾两次到京,均得到黎锦熙的帮助和关心,并一起讨论中国和湖南的"解放与改造事"。1920年5月,毛泽东由北京返回长沙,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毛泽东与黎锦熙的通信也中断了数十年。在连年战争、特务横行、颠沛流离的年代里,黎锦熙始终完好保存着毛泽东寄给他的书信《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早期革命文献。直到解放后献给国家,成为研究毛泽东早期革命思想的珍贵资料。
1948年底,黎锦熙断然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乘飞机去南京的指示,撕掉南下的通知,对家人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骤的伟人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黎锦熙还多有往来,特别是解放初期,毛泽东经常一个人跑到黎锦熙家聊天,因为和他聊天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后来,因为安全的原因,毛泽东只好将黎锦熙请到中南海做客,并与他讨论有关教育、文字改革等事。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六十余年。(王淑芳)
误金与关怀
1949年夏天,我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后,有些广东的同志希望我跟他们一道随军南下。我因为要在北京创立研究民间文艺的机构(该机构于次年春成立,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在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所以没有成行。不久,我新认识了叶丁易同志,他是一位进步的年轻的学者和作家,曾经去过解放区,这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为了想使该系增添一些新的力量吧,约我和黄药眠同志到该系共同工作。我们答应了。当时黎先生任北师大校委会主席兼中文系主任。他约我和药眠面谈。地点是西单西头的"大地"(俄国式餐厅)。丁易同志当然也在座。黎先生初次给我的印象是:身材短小,面庞瘦削而微黑,但双眼炯炯有神。他的说话略带湘音,使我联想起另一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满口流利的京音来。黎先生对药眠和我约略提到授课的科目和时数,显出他是一位富有行政经验的、精干的学者。
他约我开设民间文学课是很自然的,他在《国语运动史纲》的长篇序言中已提到我重编过清李调元的《粤风》。在这次餐桌上的谈话里,有一件事当时很使我感到诧异。那就是要我开设"方言调查课"问题。当时,黎先生谈到我将来所授的科目,他希望我开设一门"方言调查"之类的功课。我当然谢绝了,他也没有勉强我。但是,我心里总不免觉得怪异。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希望中文系里有较多的同事来开语言学方面的功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一向是搞文学的,特别是搞民间文学的。历年研发表的文章,除了文学和民俗学外,也很少涉及其他学科。这点,他大体是应该知道的(即使我自己或丁易同志没有作过介绍)。为什么他老先生竟提出那样的希望呢?原因到底在哪里?经过心里反复思考,我忽然领悟过来了。
事情的来源大概是这样的。本世纪20年代中期,我常在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和《国学门周刊》发表关于民间文学一类的文章。有一次,在《歌谣》上看到毛坤先生所译的P·马伦笃夫《现行中国之异族语及中国方言之分类》该刊89号,"方言研究号",1925·5)的论文,我觉得文中关于我国地理及方言分布的话,跟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形有出入,便写信给译者,指出错误的地方。译者写了同意我的指摘的回信,并把它跟我的原信,用《关于中国方言之分类的讨论》的题名,一齐发表于《国学门周刊》第六期。当时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它的出版物,较早的如《新潮》,稍后的如《国学季刊》以及《歌谣》周刊、〈〈国学门周刊〉〉等,在国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黎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虽然他致力的是语言方面),并且住在北京,当然是看到我和毛坤同志讨论方言的信的。因此,认为我在这方面也是个行家,所以在二十多年后请我在他主持的中文系里教书时,便想了起来,并希望我为系里开设这类的课目。
从上面的叙述看,这无疑是一场误会。但是,它是何等值得思索,乃至于何等值得感谢的误会!二十多年前,一个刊物上所登载的通信,黎先生竟铭记在心,历久不忘。这岂仅仅是记性过人而已。从我这方面说,当时还不过是一个有心向学的青年,学殖的浅薄自不待言。一时偶然写发的短信,竟引起这位前辈的注意,以至于在多年之后,见面时向我提出开设专课的希望,这是多么使我感动和铭谢的呢!(摘自钟敬文《回忆黎劭西先生》,载《黎锦熙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题目为编者加)
记得,比加倍偿还更好
30年代初期的一个暑假,我先后考上了三所大学,但只有一所是适合我这个穷苦青年就读的,那就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因为它不收学费与杂费,只在报到人学时交注册费20元。这个数目在今天看来,不算一回事,但在30年代初,20元大洋够一个大学生10个月的伙食费。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样一笔巨款,要在短时间凑齐是不容易的。那时先大兄吴兰阶从北平师大英语系毕业不久,在太原平民中学教书,收入有限,况且他刚刚结婚,还要担负两位弟弟 ——我与家三兄的生活费,一时实无力拿出这笔钱来。大哥穷极智生,因为我考取的是师大国文系,便想到当时正担任师大文学院长的劭西先生。 大哥原名吴立峰,20年代初在香山慈幼院小学部教书。1927年前后为了报考男师大的体育系,借了一位名叫"吴兰阶"的中学毕业文凭,考上之后,申请转学英语系。一面在大学读书,一面在中学兼课。以中学兼课所得应付大学的费用,这种以"师"养"生"的办法,是一些好读书而又无力付出学费的穷苦青年的创造,在当时的北京颇为盛行。大哥便是这样"穷凑合" 地度过大学生涯的。那时的师大每个班级的学生一般只有20人左右。师生见面的机会较多,关系也较密切。由于劭西先生是湖南老乡,大哥更感亲切,经常以学生而又兼同乡后辈的身份,前往劭西师的寓所西城根的烟筒胡同4号请教,年复一年地便熟悉了。我之所以报考北平师大国文系,并且做出最后的选择,都是大哥的意思。他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师大的国文系主任是钱玄同,文学院长是黎锦熙,还有其他许多教授,大多是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希望我能在"名师"的教导下成为"高徒"。二是我家四兄弟,除了二哥经商外,大哥学外文,三哥也学外文,我对外文更是特感兴趣,但是大哥说,我不能再学外文了,将来一旦亲友去世,连做祭文、写挽联的人都没有,便决定要我学中文。当然,我自己也清楚,家底薄,不能上名牌大学的外语系,便觉得大哥的话符合实际,将来"一间三学士",虽然很风光,但要请人写祭文,做挽联,也是一大缺陷。那时我的思想水平就这么高,并无今天的青年要献身共产主义的祟高理想,便同意了大哥的决定,由他请劭西先生解决经济困难。在截止报到的先一天,大哥带我到烟筒胡同4号拜见劭西先生。劭西先生当时40刚出头,竟然自购了那么宽敞的住宅做"公馆",的确使我这个穷书生莫测高深。大哥点破了一句: 劭西师收人在大洋600元以上,儿子在欧洲留学。我才"呵"了一下。我们兄弟被女佣引进南屋的客 房,当中一架钢琴,闪光发亮,似乎流动着音乐的语言。我们刚刚坐稳,劭西先生含笑而来,手托烟斗。大哥首先介绍,劭西先生笑嘻嘻地说:“你的文言文有根底嘛,钱先生也说写得不错。”又对大哥说:“前天你谈的注册费事,我已招呼过注册组,由我担保,将来扣我的薪水。”大哥连声道谢。次日我便到和平门外南新华街的北平师大报到。大哥说:“师大是培养教师的,你将来能做一名称职的国文教员就行了。”做一名称职的国文教师,是大哥对我的要求,这个要求并不高;但真要做到"称职"的程度,又谈何容易!
四年的大学生涯很快过去,芦沟桥的炮声冲散了劭西先生与我的师生关系,他前往西北,我流亡西南,但书信联系,却从未间断。抗战胜利后,曾在南京多次拜见。南京刚解放,承他函约赴京,得以亲睹开国大典。有一次聊天,我谈到当年承蒙他担保与借款的事。由于事隔十来年,他乍一听,似无反应,经我旧事重提,他才"哦"的一声地笑着说:"人情不是账,算账还不清。你记得就好了,记得比加倍偿还好得多哇!" 劭西先生吸了口雪茄,喷吐长条的白雾,我想:这漫长不断的烟雾,不正象征着师生之情么!我于是强调地说:我记得,永远记得。劭西先生笑了,我也笑了,坐在一旁的贺先生也笑了。(吴奔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