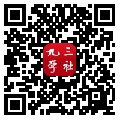新中国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代学子,识字之始,大概没有不从那本《新华字典》获益的。然而,若是现在要问起这本小小的《新华字典》为谁所编的话,恐怕则鲜有人知了。虽说我们常有“饮水不忘掘井人”之旧训,但天长日久,“掘井人”难免还是会被遗忘的。这位或许已被遗忘的学者,就是北大著名教授、九三学社早期社员、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
也许有人会说,字典工程,严谨浩繁,仅倚一人之力恐难以完成。确实如此,但魏建功先生作为《新华字典》的开山人物却无人可替。早在1950年初,魏建功与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商议后,辞却了北大中文系主任一职而任出版署下的新华出版社社长,就是为全身心地主持《新华字典》的编纂之事。之后历时三年余,由魏先生担纲主编,这部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华字典》,终于1953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后虽不断地修订、改版、完善,但魏建功先生对现代汉语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则是永将载入史册的。
如今,知道魏建功的读者确实不多了。其实早在后“五四”时期,身为北大学生的魏建功就已经小有名气了。他是鲁迅的崇拜者,大二时就选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而且每次都是坐在第一排听讲。但也就是此时,为了一篇刊登在《晨报副刊》上反驳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文章,他却受到了鲁迅先生的严厉回击。然而也真是“不打不相识”,事后鲁迅通过了解也表明那只是一个“暂时的误解”,从此他们开始交往,保持了非常深厚的师生情谊。1934年,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时,要求甚高的鲁迅,却十分赞同将那篇序文请魏建功用楷书抄录,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魏建功人品及书品的认可。
魏建功先生擅篆书、楷书与章草,他书法的功底得力于他毕生研求的文字学。大凡殷商甲骨、两周金文、秦篆汉隶、魏碑晋书等,他都会悉心揣摩,得其神韵。魏先生对文字学的爱好自少年起就养成,那时他就读的南通中学,是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状元张謇所创办,该校有诸多“货真价实”的名师,使魏建功大受其益,14岁的他就喜欢听先生讲《说文》、《尔雅》,受几位中学教师的影响,他对文字的源流、文字的形音义以及方言等都格外的感兴趣,至中学毕业,就将文字学作为自己毕生的学问研读方向了。等到就读北大时,魏建功更是如鱼得水,那时北大的国文系,可是个大师荟萃、名流扎堆的地方,像马幼渔、沈尹默、钱玄同、黄侃、胡适、沈兼士、周作人、刘文典等等都在国文系任教,已发表《狂人日记》和正陆续发表《阿Q正传》的鲁迅先生也在北大兼课。这给了魏建功转益多师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在文字训诂和声韵学方面,他师承钱玄同和沈兼士,钱、沈两位均为文字音韵学领域里的顶尖学者,造诣极深又颇多著述。而魏建功聪颖的领悟力以及学问上大胆开拓的独立精神,深得钱、沈两位业师的赏识。1925年毕业时,由于他各科成绩均列班上第一,故被沈兼士教授封为“乙丑科状元”之称号。多年前,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回忆说,三十年代他在北大就读时,也曾选修过沈兼士先生的“音韵学”,考了六十多分,很是得意,不料沈先生在课堂上“训斥”说:“你们考六十多分算什么,魏建功上我的课时,他考一百分!”言语中,对拥有魏建功这样的高足充满着自豪。
我读过数幅魏先生的书法,多为楷书和章草。其楷书学乃师钱玄同,也是走唐人写经的路子。但钱玄同的字是以北魏书法的底子,参以清人邓石如的阔厚,写来比较舒展、宽博;而魏建功之书,同样是写经体,则以隶书笔意写楷字,虽没有钱师的豪放,但却是端庄间见灵动,古茂中含秀逸。至于魏先生的章草,倒也别有一功,虽能看出得“史游”、“皇象”之法乳,但他更多的也是以隶书笔意写行书,有时通篇观赏,一波三折,颇感烂漫天成,不失文人书法之雅趣。
精于文字之学的魏建功先生,学问之余也时常耽于书法篆刻的研习,深得师友朋好之赞颂,除了为《北平笺谱》手书序文外,还为刘半农以及罗常培书写墓志铭等。鲁迅先生逝世后,为了纪念恩师,他发愿要将鲁迅先生的旧体诗手书刻版印行。后来长卷虽已抄好,但未及刻版印刷,旋即抗战爆发,于是,他就随身带着这幅长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教学生涯。此后又遭长卷丢失以致计划搁浅,事后虽二三十年过去,但此“心愿”未了,成了他耿耿于怀的心中恨事。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在魏先生下世十多年之后,长卷居然失而复得,于是,在1996年,由魏建功手书的《鲁迅先生诗存》,终于经江苏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此一大喜讯足以告慰九泉之下的魏先生了。
至于书法之外,魏建功还擅刻印则更是少有人知。其实早在北大执教时,魏建功就和台静农、常维钧等几位爱好者成立了“圆台印社”,并邀请了王福庵、马衡作为他们的指导顾问,也可谓“师出名门”了。可惜香港马国权先生的一本《近代印人传》,虽收了清华闻一多,却失收了北大的魏建功,未免稍有缺憾。说来有趣,魏建功刻印,还开创了一件稀有印材——藤印,为印坛所未闻。抗战时魏建功在昆明西南联大,闲时尤喜为朋友刻杖镌筷以遣兴。那时当地所售的皆是越南白藤手杖,其断面似桃形,细腻而多棕眼,于是魏建功便将藤杖一段段锯开,在其断面上刻印,不料刻成后大受欢迎,魏建功也为自己开创了一件新印材而得意,兴之所至,频频治印送人,别具情趣。后他将所刻的藤印还专门辑成一册《何必金玉印谱》,并道:“天地间堪充印材者何啻百千,富家儿持金逐玉,争奇斗艳,实则败絮其中;君子安贫乐道,但得印中三味以陶冶性情,又何必鸡血田黄?”
这实在是文人的雅兴所为了。魏建功先生非职业的印家,故他的印章里,自然有一种文人的趣味。大收藏夹张伯驹先生曾为他的“藤印”作品题写七绝两首,其一为:“不须砍作邛竹杖,直为摩成汉殿砖。钤入丹青画图里,苍茫犹带五溪烟。”
魏建功先生是一位宽厚正直的学人,然而,正直的人也往往会受骗。建国后的北大校园中,学生们曾给魏先生起个外号叫“跟党走”,这大概就是嘲笑文人迂腐的一面吧。然而,无须回避的是,在“文革”后期,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等几位教授被点名进入了“四人帮”直接领导的“梁效”写作班子当顾问,专门注释“孔孟”及“法家著作”等文史工作。本还庆幸自己一生研究的文史知识,终能在新时代的革命工作中派上用场,不料“文革”后则被指责为“爪牙帮凶”或是“谄媚江青”的“污点”而为人所诟病。尽管有着“跟党走”之外号的魏建功,却不料“晚节未保”,一步不慎还是“跟”错了。
为此,晚年的魏先生郁郁寡欢,承受了政治和健康上的极大压力,后终于1980年逝世。在魏老的追悼会上,老友王西徵撰写的一副挽联还是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联曰:“大千界桃李芬芳,讲坛由来多花雨;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
这最后一句“毕竟是书生”,则体现了友人对他这样一位文人学者的宽容。后来,同为“梁效”成员的著名史学家周一良,也用这句“毕竟是书生”,作为自己回忆录的书名。(《上海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