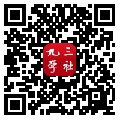敬爱的金开诚先生于2008年12月14号6点50分去世。金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北大书法所所长。他在北京大学工作了50年,我和他有20多年的学术交往。金先生的离去让我们感到不仅是北大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和书法界重大损失。
薪火相传 学术人生
金先生的乐观大度使人们没有意识到病魔的出现。去年4月,我发现他脸色越来越不好,尤其是4月下旬给研究生上课,他讲到最后说他很累讲不动了。在我的印象中,多年来,他去人民大会堂和各种会场开会,都是声若洪钟惊四座!到了今年五月四日北大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和北大校庆110周年书法展在北大图书馆开幕时,我近距离地站在先生旁边,才发现他脸色不好。我就提醒说:先生您脸色不太好。他说:我一直发低烧。我说:那可要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海外大学任教,等到我7月份回来的时候,他夫人和女儿告诉我说他6月做了手术,我当时很震惊。马上赶到医院。一见面他就说:我这次得的是癌症,我年龄也大了,吉凶难料。我说:先生别这么想,手术不是已做了吗?癌症病人很多,很多人都会得这个病的,他们大多数不是渐渐好了吗?我说,同学们还等着上您的课呢。结果,没多久先生就出院了,我心中很高兴。再见面我感觉他明显瘦了好多,起码瘦了20斤。
只过了一个星期,先生又发烧住院治疗,病情更严重。我又一次到医院去看望先生,这次去见到的情形很不妙。我看到先生正处于昏迷状态,鼻孔插着氧气管,他女儿舒年守在床头。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我想他也许会醒过来。他女儿说:这不是睡,是发烧,体力不支,处于半昏迷状态。这次见面后,金老师就再也没出过院,那是10月份的事了。到了11月初,金先生病情更严重。我带着第二届书法班的王云龙、叶龙、刘枫几个同学去医院。而且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一进门他看见我,眼睛特别明亮锐利,说:你来了!我说:我来看望您来了。他大声说:我要坐起来!我说:先生你别动,您好好躺着就行。他不同意,拉着我的手,攥得特别紧。我觉得他想传达一种想法,一种力量,想表达他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我使劲把他扶起来,心里很难受。但先生半坐着什么也没说。我能理解这种生命的茫然——见到很熟悉很亲切的人时,他头脑清醒想跟你表达某种生命深层感受,但病体衰微又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学生们回来后说,自己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这样一位病重的老人,他一心为了工作,一心为了他人,一心为了国家,一心为了中国文化的崛起,一心为了将中国美好的东西传出去和传下去。
关于2008年11月8日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的中韩书法展,我问病榻上的先生有什么意见,金先生强支病体说,这种国际书法展很好。并对看望他的学生说,“我明年还给你们讲课。”但我们都知道先生可能等不到明年了。因为他是6月做完手术后,医生说超不过半年,而且这段时间医院发了三四次病危通知书。
按照中韩展出计划,我率领北大书法所代表团12月14日早晨8点20分飞往首尔。飞机降落后,我开机一看是金舒年发来的噩耗:金先生于今晨6:50病逝。巨大悲痛使我一下就怔在韩国机场。我告诉大家金先生去世了。曾来德教授和同学们都很吃惊和悲伤。我给书法所人员布置悼念活动,给先生家属发了唁电,给校领导汇报情况。
12月15日韩中第十四回书法交流展在光州双年展大厅隆重举行,展厅里韩国来了大约200位书法家,我在会议上宣布了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以后,韩方的主持人宣布,集体为北京大学书法所金开诚教授默哀。看到那么多外国人为中国的这样著名学者、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默哀,我感到了一丝欣慰。
韩国3天之行结束后,我们一行4人17日下午回到北京,我马上给舒年打电话,代表书法所全体师生向先生志哀。她说:先生走得很平静,按父亲遗愿,一切从简,21日上午9点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回顾金老师在人生的最后这段日子,我认为先生是很坦荡的,视死如归,他没在我面前说过痛苦。他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最艰难的时间里,完全靠坚强的意志维系生命。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刚做完手术住院的日子,他居然躺在床上跟他的女儿口述文章。就这样,他还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等报纸上。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金开诚先生在学术界、书法界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他做学问和写书法都很严谨,他在韩国出《金开诚文集》四卷,尽管他眼睛不好已经不能自己校对,但他对排版错字盯得很紧。我深刻意识到为什么叫“校字如仇”。有人认为出一本书就是荣誉,其实出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你的政敌立一个把柄,为后代留下笑柄。对此,金老师说了8个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金老师是一个专注于精神的学者,对自己的生活不甚在意;先生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一个得到别人的恩惠就会经常去感谢的人;先生是一位澹定坚强、无欲则刚的蔼然长者。先生对学术和艺术体现了8个字——惜时如金,疾恶如仇。他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对自己是惜时如金,对社会和艺术界的不良现象是疾恶如仇。
金先生备课超出常人地认真,讲稿上那细细密密的小字密密麻麻地,而且对着镜子录音练习讲授,他几乎把自己讲课的每一段内容都背下来。我有时候很疑惑地问:先生口若悬河,文惊四座,为何还要这样费心备课?他说:哪怕是成了教授博导,也要像青年教师第一次上台那样小心翼翼地去上课,这才是上课的本质。如今一些人上课已经是开始随便聊天闲扯,但这么多年来,先生讲课的认真严格的程度没有丝毫改变。
金先生在北京大学书法所授课期间,研究生班的学生并非正式招生的硕士或博士,他们进入北大就带着敬仰的眼光看待北大名教授。像金先生这样的北大重镇级教授,很多教授已经不上大课。然而金先生却坚持连续几天上大课,上午3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金先生去世后我对学生们说,先生是为你们累死的。记得每次上课后下午5点多钟,我开车送他回家,从反光镜中见他坐在后座椅上,面色憔悴,极度疲劳。一位70多岁的老人,能够一天连着上6个多小时课,中午只是简单地吃顿饭,这种人格襟抱是多么难得!
金老师在无锡一所大学做书法所所长,他经常到无锡给大众讲演。他有一次跟我说,自己开创了一个先例,就是不收费讲演。我说这很难啊,今天的经济学家出场费动辄好几万,像您这样的名教授,收费标准应该也很高。他说我就不收费,我一定要纠正这种恶劣作风。他在无锡面对市民和干部,创立了这样一个长期的免费讲座,受到了热烈欢迎和好评。在一切都以商品和金钱来衡量的当代社会,金先生的这种人格境界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
北大很多教授都非常忙,号称空中飞人,对学生的论文看得也不是很认真。我出席过很多博士硕士论文答辩,可以说一些导师对学生论文并不认真,对其中论题、文字的错误等没有纠正。金先生和我在书法所招收了一位研究生,先生看论文时眼睛很不好,买了个高倍放大镜,逐字逐句地读。后来把这个学生叫来,金先生提了近百条意见。先生学问是巍巍高山,但又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在一点一滴中让人感受到其人格魅力与精神滋养。那个学生一改过去狂态,说从此以后为人为学要向先生学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什么要这样做?先生告诉我,这叫做爱惜羽毛,一个人从黑色的毛、杂色的毛,好不容易修炼成白天鹅,通体白色羽毛,但稍不留神,一点污渍,一泼脏水,就能污染了羽毛。所以为人为学,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金先生为北大书法4周年题词:“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不能只靠北京大学‘金字招牌’吃饭。既然书法界是个名利场,那么我们的特色就在于偏不计较名利!我们要大讲为弘扬祖国的标志性艺术——书法作奉献,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奉献。我们一无人员编制,二无经济来源,三无活动场所;但‘至少我们还有梦’。我们还有笔墨纸,我们就要拿笔墨纸来做这个奉献之梦。” 金先生很关心书法的国际交流,认为北大书法所提出“文化书法”,主要就是从事书法的国际交流,要将汉字的审美化书写国际化,先生跟我说,一定要走出去,中国书法如果自己关起门来,变成一个退休老人玩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了;书法必须要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当这么多的外国人学了汉语和汉字,拿起毛笔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文化就如春风化雨般点点滴滴输出去了。
金老师为中国学术文化和中国书法文化的崛起鞠躬尽瘁,不幸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倒下了,他应该像季老、文老那样活到100多岁。先生曾和我说过,北大就看两头,一个是口头,一个是笔头,此外都不重要,以先生的口才——文不加点,以他的笔才——立马可待,定会取得更高的成就。可惜天不假年,不想先生就这么走了……
先生曾经跟我说:我不怕古人,我就是研究古人的;我也不怕名人,我本人也比较有名;我更不怕前人。我问那您怕什么?他说我怕后人:不畏先生畏后生。前面一代先生的墓志铭是由这一代书写的,先生这一代人的墓志铭也将由后人书写。他通过点点滴滴地人格修为和精神践行,将自己的音容笑貌留存人间,留在了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永远感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