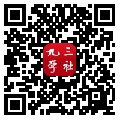金开诚先生的辞世,让广大后学无比怀念。他的卓越学术文化成就和对国家社会的重要贡献,不仅在我国上层经典文化学界有相当高的评价,也在我国民俗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金先生曾与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交谊甚深,而金先生小钟老32岁,却在钟老百年身后的7年便匆匆离去,这是让人十分痛惜的。他带走了那样真诚炽热的爱国深情、那样深厚精粹的学问积累和那么富有才华的中国文化传承气象,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金先生认识我和教导我,是与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俗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历程紧密相关的。我在文革后上大学、考研究生,师从钟老读民俗学专业,后来又当钟老的助手,在其中的很多环节上,金先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与钟老的莫逆之交和与北师大的渊源关系,让广大钟门后学受惠多年。
1949年,钟敬文教授响应党的号召回到祖国,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3年,钟老招收了全国第一批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1955年创立了全国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就在这一年,金开诚先生成了北师大的“姑爷”。钟老当时对中央高校规划纲要中的民间文学教育体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但同样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并不能一一实现,甚至还曾与金先生的老师游国恩先生产生过学术争论,对此钟老自己也说过:(将来)“有人在谈话里提到这段历史上的小风波的时候,我们将用回顾自己孩童时代行径的那种心情去给予爱抚的微笑罢”。实际上,在上世纪50年代,前辈学者大都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中国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他们重视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钟老那时也要求弟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地对中外学术文化遗产。他还经常在周末带领弟子逛旧书店,或者上香山、去颐和园,对培养新中国民俗学人才倾注了很深感情,这时金先生都跟着参加,他谦虚谨慎,又不复依傍,往往语出惊人,所以深得钟老赏识,一老一少私交很深,改革开放后,钟老发展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提倡从中国整体文化观的角度研究民俗学,并提出建立民俗文化学。这时金先生也已成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和传统文化史的名家,他们经常在报刊杂志上撰文唱和,彼此关注。而从中国民俗学的建设说,金先生在这一阶段中的历史功绩是尤其需要铭记的。
首先,他在游老和钟老之间,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民俗学这两门顶尖理论研究的大师之间,架起了桥梁,对二老生前没有机会共同解决的一些问题,给予了解决。他还对游老的学问加以发展,主要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古代经典和下层文献加以综合研究,这使他能始终把握国家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对政府公共文化政策建设提出大量有价值的建议。他对钟老学问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发展,主要是能从现实实际出发,关注文化史家和民俗学家都不一定注意到的现象,要求重视社会变迁的实际,这样他就不是仅盯着历史规律,还能关注具体的变动,深入到具体对象的社会活动中去研究,这样的研究就能提供历史现象重组的机会,产生学问上的创造力,他常说“知识能用,才是力量”,受他的启发,我认识到,一门学问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理论运行的实践性,这也正是金先生与前人学问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次,金先生是中国民俗学近年改革实践的功臣。我在师从钟老念书期间,金先生的中介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金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摸索了一套教学科研的绝招,它们同样适用于文革后北师大民俗学专业青年人才的培养。钟老经常让我去找金先生,还几次请金先生来北师大讲中国传统文化课,观察金先生的讲演在同学中引起的轰动效应,然后再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进行教学改革。我于1985年完成硕士论文答辩,1989年完成博士论文《明清民间文艺学史略》的答辩,这中间不知跑了金先生家多少趟。他通过帮助我,实际上也等于辅助了钟老的教学,这对于钟老晚年来说,真正是肝胆相照的援手。在我博士论文答辩时,金先生经钟老的“钦点”被委以重任,既当博士论文评议委员,又当答辩委员会成员,另一位九三学社的前辈启功先生也是本次答辩委员会的委员。而金先生的出力相助,的确给北师大的民俗学创新教育增添了实力,也带来了新思路。1993年,北师大成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钟老特邀北大著名学者季羡林、张岱年、费孝通和金开诚先生一道,加上其他9位国际同行中的一流学者,共同担任特约通信研究员,这其中对金先生的爱重不言自明。1999年和2000年,北师大以“中国民俗学教育的改革与实践”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金先生更是功不可没。
第三,金先生是中国民俗文化国际交流事业的有力支持者。金先生凭着深厚广博的学问积累和钟老学问的透彻了解,不仅在国内学界扶侍钟老,也在海外文化推介上为钟老大声疾呼,不遗余力。一次,他应邀为钟老的新著《芸香楼文艺论集》撰序,几十万字的书稿序言不出半小时写完,思想深刻又文采飞扬,大有裨益于钟老此著的对外交流,钟老为此逢人就夸“金开城,大才子”。后来启功先生听说此事也盛赞云:“唐有李白,今有金开诚,文章八千言,倚马可待,无人能比”。钟老在对我的培养教育上也强调吸收世界先进学术成果,而我两度出国留学的推荐人都是金开诚先生。当他在“与被推荐人的关系”一栏中填上“师生”二字时,我的感动无以复加,因为我深知这是一种殊荣,在他并不求回报,而在我却必须用一生的努力来回答的。
现在金先生已与钟老去了同一个世界,两位恩师一定在对祖国和对后人无悔无怨地的奉献中从容相谈,生者的怀念不也应该因此而化为前行的动力吗?敬爱的金先生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