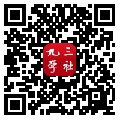华西坝联大大学生

薛愚伏案工作
薛愚(1894—1988),药物化学家、药学教育家。湖北襄阳人,1925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化学系,1933年获巴黎大学理科博士学位,回国任河南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主任;1946年参加九三学社。1949年后,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教授,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编著有《实用有机药物化学》《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实险教程》《医用有机化学》《中国药学史》等。薛愚对中国的药学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中国药学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
战时后方的文教中心,除了昆明(西南联大)之外,尚有“三坝”——汉中的古路坝,重庆的沙坪坝,和成都的华西坝。其中以成都华西坝条件最好,被称为“天堂”;重庆沙坪坝次之,称为“人间”;而陕西汉中条件最差,被戏称为“地狱”。薛愚随齐鲁大学迁至成都华西坝,继续开拓阵地,他回忆道:“1939年到1944年我在成都齐鲁大学任教,是我从事药学教育的重要阶段。”
1937年底,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一时间,机关学校、文化科研院所、社团商会,以及颠沛流离的民众,纷纷涌向西南腹地,趋避巴蜀。齐鲁大学也服从“迁校抗战”政策,除部分员工留守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成都。
“华西坝上五大学”
1938年,齐鲁大学医学院师生已抵成都,与华西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联合开课。1939年,齐鲁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部分师生和校长也陆续抵达,他们“是赤手空拳去的,既无仪器设备,又无图书资料,更缺少教师”。文、理学院的院长由校长兼任,理学院有生物、物理、化学和数学四个系,除生物系外,各系都没有负责人。薛愚被校长任命“为化学系负责人,准备恢复重建化学系。”此后,薛愚在院系建设方面的“特长”在此得以施展。
拥有一流校舍、教学设备及临床医院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先后接纳了西迁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三大医学院联办医院,优势互补,成为战时中国的医学教育和临床中心。齐鲁大学是基督教会在中国建立的最早的大学之一,迁校后,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部分校舍复校开课。随后,南京的金陵大学(迁校后薛愚同时也在金陵大学授课)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迁至华西大学,5所教会学校共同组成“教会联大”,时称“华西坝五大学”。
“教会联大”的性质属于“教育共同体”。据记载,“教会联大”5所大学人员达3000余人,共有文、法、理、医、农5个学院,近70个学系。而当时,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并组的西南联大,同样是5个学院,学生也在3000左右,但只有26个系科、2个专修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华西坝联大”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薛愚回忆道:
“由于五个大学都集于华西坝,基督教会支持出资添建了两座楼房,即办公楼和化学楼,化学楼由五个大学理学院的化学系分占。齐鲁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只占用一小部分,仅有一个小的办公室和两个较大的实验室。后又逐渐购置了仪器设备,聘请了教师。除无机、有机、分析、理论化学等之外,全部借教于金大和华大。当时我教有机化学,也是几个学校联合听课,约有100多学生,教学工作逐渐完善。”
不仅设施一流,同时华西坝名家汇聚。除当时各校校长(金大陈裕光,金陵女大吴贻芳,齐鲁刘世传,燕京梅贻宝,华大张凌高)外,人文学方面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顾颉刚、钱穆、蒙文通、吕叔湘、常燕生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等,都在此执教。
除固定授课之学者,“教会联大”还广邀世界知名学者来演讲交流。如1941年春末,美国作家海明威曾在华西坝体育馆演讲;1943年,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更在教会联大展开超过20天共计12场的演讲。还有许寿裳、张东荪、周太玄、孙伏园等名家也曾在“教会联大”授课。
“教会联大”教学体制也十分先进。蒋梦麟在早年回忆录中提到,“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效率,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这些机构的人才多数来自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引进欧美教育制度,与教会所在国的一些名校有着教学、科研和师资等方面的联系,例如金大与美国康奈尔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都有密切的校际合作关系。
蒋经国曾忆及1941年在华西坝的见闻,“我们看到华西坝的坚固和管理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华西坝是外国人经营的,那里非常清洁整齐,我们参观了华西大学,再反过来看一看成都,好像是隔了两个世纪。”李约瑟称:“该大学令人称羡的是校园里中西合璧式建筑,它是当今‘自由中国'所有大学中最好的,该校友好地接纳了另外四所疏散于此的其他大学……”并曾特别提到,“在齐鲁大学,对薛愚教授对抗疟疾药物的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颇感兴趣”——薛愚的学术实力可见一斑。
“哪里需要哪里搬”
薛愚除当时在“华西坝联大”授课,也曾在西南联大授课,开数门课,当时亦有一些非议,讽刺薛愚是“通才”,但薛愚不以为意,“旧中国教育的落后是全面的,故大学里学生需要什么科目,就应该开设什么科目,教授就是要做到哪里需要哪里搬”——薛愚先后讲授过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普通化学、法医化学、药剂学、调剂学、药学概论等数门课程,确实做到了“哪里需要哪里搬”。
如薛愚所言,当时5所大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教师跨校讲学,学生自由选课,学校间互相承认学分——这种体制极大地利用了有限的教育资源。
但与南京迁来的两所学校相比,齐鲁大学自山东中西部向西南大后方移动异常艰辛,许多重要的教学设备都无法随行;许多山东籍教职员也因家室原因并未搬迁,或由于日军封锁长江交通,只得由青岛乘船至上海,由上海辗转至香港,再乘轮船至越南西贡,然后乘火车到昆明,再乘汽车到重庆,最后到达成都,费时数月,行愈万里;至于学生,则完全采用流亡或逃难方式迁移,故齐鲁大学迁至成都时已元气大伤。
白手创业 创建药学系
齐鲁大学千里迁校导致的“先天不足”并没有使薛愚灰心,反而更激励薛愚“白手创业”,决心在齐鲁大学创建药学系。但校方要求薛愚恢复化学系之后才能着手创建药学系,因此这项工作从1940年才正式展开。薛愚回忆道: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慎重起见,我请教当时在成都卫生界的两位教授,想不到一瓢冷水浇到我的头上,他们说药学不是科学而是技巧,刷瓶洗罐、数药片而已,要什么药学系?你把理学院办好,把化学系搞好就够你忙的了,药学系干不得。这使我回忆起自从我留法回来以后,在摸索开展药学教育的道路上所听到的‘中药用水煎熬之后,倒出药液,几分钟就可化验完,还要什么研究’;‘现在中国人民需要吃饭,不需要吃药’;‘药学是搞草根树皮的,乡下老太婆也干得了’。”
“我真是莫名其妙,疑惑到底什么是药学?难道药学在国外是甜的,到中国就变苦了吗?我爱药学,爱药学教育,因而下最大的决心,要为中国药学事业做出贡献。但是当时中国的药学事业实在是处境维艰。辛亥革命以后对药学即轻视,对中医中药歧视;蒋介石通过了‘废除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以后又提出什么‘废医存药’论,实际上还是变相地废除中医中药……中医药备受摧残,那么西药的发展是否就有前途呢?否。欧美传教士在中国亦大量倾销药品,而我国却没有药学教育基础以培养药学人才。”
据薛愚调查研究,例如1842至1920年,全国有教会医疗院处等250个之多,其中没有一名中国籍的药师或药剂人员,都是洋人。又如,至1897年,我国教会医院有60所,其中有39所兼收生徒,但没有培养一名药剂生。
而中国自己创办的同文馆(1865)、天津的医学馆(1887)、北洋医学堂(1902)、京师大学医学实业馆(1903)、京师专门医学堂(1906)等均没有设置药科。至抗日战争前,中国自办的医学校33处,药科只有4处。“自1906年陆军医学校添设药科开始至1936年止,三十年中,旧中国培养的药师,登记者不足400人,平均每年仅十余人。由此可见对药学校和药学人才的培养极不重视。”
薛愚一方面不为眼前的“阻力”所动摇,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对药学的歧视,不仅是药学自身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的隐患。药品独立生产有两大重要意义,一是战时可以不受别国制约来保障伤员用药,二是平时可以不受外国企业经济上的压榨而保障国民用药,可见药品生产绝非一般实业,而是影响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
明确了“制药以救国”的思路,薛愚也获得了无穷动力。他说:“根据前辈药学工作者和社会贤达的意见,以及当时社会现实与人民的需要,我个人进一步肯定药学是科学,它和医学同样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二者缺一不可。于是决心与华西大学制药系协作,借助它们有关药学方面的设备和师资。基础课如物理、化学、数学等是由齐鲁大学理学院担任;生理、药理两校合作开设;生药、药剂、调剂则借助华大药学系,在互相协助合作的原则和精神指导下,齐鲁大学药学系终于办了起来。”
薛愚广泛聘请教授、购置仪器药品、查阅自辛亥革命起的药学文献以完善教学资料,为药学系四处奔走,鞠躬尽瘁。在教材编写方面,薛愚1937年完成《实用有机药物化学》一书,但由于抗战关系,直至1941年才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第一部专业药学教科书,后数次再版;1938年在国立药专任教时编写的《普通化学和定性分析实验教程》一书,也于1941年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是我国第一部实验教程;与林启寿合编的《药物化学》也送交国立编译馆进行审定。薛愚夫人张英侠回忆,在看到第一届毕业生时,薛愚“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本文转载自《团结报》2020年12月24日 07版 作者 孔瑶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