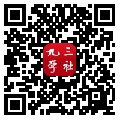19岁站上大学讲台,29岁失明,人生舞台大幕逐渐合拢。
阅读和书籍,让我看见生命航行中的灯塔。
黑暗中奋斗,登上哈佛大学演讲台,重回三尺讲台,播撒点点星光。
——杨佳
沐浴在科学的春天
我是个湘妹子。
故乡的山山水水令人难忘。
从我家窗子望去就是岳麓山的美丽景色,从小我就爱跟父母去爬山,一路走来,岳麓书院、爱晚亭、黄兴墓、白鹤泉……
我的童年不仅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的岳麓山为邻,更与靠窗的4个竹质的大书架为伴。
1978年,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一下子我的同学们都秒变“追星族”,大家争相立志要当科学家。
那年正赶上全国恢复高考,学校让我去试试。我想,试试就试试!
我是穿着一件印着“Spring of Science(科学的春天)”英文花体字的确良衬衫走进大学校园的。
77级、78级的大学生有个特点,年龄悬殊,有30多岁的,也有15岁像我这样的,有兄妹,也有夫妻。

大学毕业前夕同宿舍好友合影(前排中间杨佳)。
这是我国积淀了十年的精英。
当时有个口号“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我们同宿舍7个人,我睡上铺,学校晚上9点钟熄灯,可半夜醒来,发现室内仍有灯光,低头一看,原来下铺的刘京鸣同学头戴一顶矿工帽,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这种精神感染着我,我懂得了什么叫紧迫感和使命感。
大家学习非常自觉。
精读课上,老师讲《镭的发现》,我们早已通读《居里夫人传》;
泛读课讲《呼啸山庄》,我们会把勃朗特三姊妹的书都拿来看;
一次,学的课文是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小说《根》,大家就争相阅读《飘》《汤姆叔叔的小屋》。
看了电影《雾都孤儿》,大家又纷纷阅读狄更斯的原著及《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
19岁的我站在大学讲台上,教英语系二年级精读课,台上台下,年龄相仿。
后来,又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当年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毕业后,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培训中心任教,也是该中心第一位教英语写作的中方教员,由于教学效果好,美国主任保拉·沙布亚克让我连教了8个学期。
暴雨洗劫的夏天
可偏偏这个时候,我的世界朦胧起来。
先是上课时读课文读错行,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合拢……
原来我患了一种罕见病,视力不断下降,失明将不可逆转。
医生把诊断结果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夜白头。
周末和假期,我不再去图书馆了,而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奔走在求医问药的路上。
西医、中医、针灸,就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都尝试了,都无济于事。
当新办好的国家图书馆的借阅证递到手中,我已经看不清自己的照片了……
终于,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迎接我的是一片漆黑。
那一年,我29岁。
适应黑暗的过程是一种煎熬。多少次,我习惯性地拉开窗帘,“天,怎么老不亮啊!”
宗璞在《告别阅读》中的那种痛心疾首,此刻,我感同身受。
然而,我坚信人类当“告别武器”,但绝不可告别阅读。
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
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30岁的我,盲校不收,只好通过电话向老师请教。
原以为盲文是一种世界通用语,其实不然。
“中国盲文之父”黄乃先生一人就发明了两种汉语盲文,世界上的盲文多种多样。以手指摸代替眼睛看,实在太难了。
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多小时,就是不解其义。
我有一个梦,我还想教书。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
第一关就是行路难。
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年复一年,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
我还想写书,开始尝试电脑语音软件,苦战数月,书一本本出版,我又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从未悲秋
在人生最绚丽、最张扬的迸发时刻,无暇沉溺感伤,唯有不负韶华,砥砺前行。
新世纪,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提出的“亚洲一流、国际知名”目标感召下,我又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还想读书!
我考上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哈佛学生阅读量非常大,每次课老师布置的阅读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就更不够了。
因为我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页扫进电脑,再通过读屏软件把内容读出来。
这样一来,时间全没了,只能拼速度了。
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单词,提速到每分钟近400个,声音全都变了调。
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 paper,还要参加许许多多的学术活动……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
最终,我不仅完成了学习任务,还超出学校规定,多学了3门课,成为哈佛大学建校以来首位获MPA学位的盲人学生。
哈佛学成归国第2天,北京申奥成功,年底中国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种大环境下,在我的导师李佩先生和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在中国首创《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课程,将哈佛MPA课程本土化。
课程放到网上,创下了中科院研究生院“空中课堂”点击量第一的纪录。我讲授的课程被评为“优秀课程”。
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专家顾问期间,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制定了“NP3S”专业服务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
我的经历表明,书不但可以看,还可以听、可以触摸。
狂歌一冬
失明让我懂得,人最怕失去方向感。也赐予我一大命题,当人生到了至暗的时刻,应怎样超越,怎样逆袭?
独处之时,思绪纷至沓来,我时常想起导师李佩和她的丈夫“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想起父辈们的创业之路。
为了制造原子弹,当年我父亲也曾与莫斯科大学专家在全国各地寻找铀矿,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任何防护设施,只有一件雨衣。
于无路之地蹚出一条路,于无望之际用性命呵护希望之火,他们为之奉献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硬实力”,维护了世界和平,从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爱在天际。
如今,以李佩、郭永怀先生命名的星星在闪耀,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做“留得残荷听雨声”,而做“映日荷花别样红”!
阅读让我与历史先贤和广阔天地对话,让我看见指引生命航程的灯塔,指引着我去追求、去奋斗、去活出人生的意义。
书籍是思想的海洋,装载着人类文明,让人觉醒,让人类的悲喜相通,围堵着的人心在阅读中奔涌而成江河,深不可测的岁月在先哲的回声中演奏着命运交响曲。
2008年11月,我在联合国总部纽约接受CRI驻联合国站记者沈汀的采访,由此与这位CRI品牌栏目《美文阅读》(More to Read)主持人建立友谊并成为其忠实听众。
他的读书标准是“宁缺毋滥”,“一旦读到自己觉得没太大价值的书,建议尽快放弃,另觅好书。毕竟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杨佳在联合国总部门前。
哈佛同学余际庭也给出三点忠告,“读跨界的书、纸质的书、经典的书。”
理由是一个人要健全其精神,首先要读跨界的书。
学文科的,应该读一些科普书籍;学理工的,应该读一些人文类书籍。无论什么学科背景,都应该读一些历史、哲学类书籍。
其次,要读一些纸质书。我们每天通过手机,获得大量碎片化的知识。长此以往,容易浮躁,满足于快餐式阅读,导致思辨能力下降。
读纸质书,不仅可以让人获得系统化的知识,还会令人内心宁静。
第三,要多读经典。经典是人类精神的巅峰。
读经典,就是让自己站在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巅峰,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精神世界,提高思辨能力,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也可以塑造个人气质,令人终身受益。
中国科学院大学创始人严济慈先生在《法兰西情书》中说,读一本书,应掌握其精髓,联系实际,反复应用,熟则生巧。
他敦促大家多去图书馆,博览群书,用时能信手拈来。
在人际交往和阅读中,我的阅读观也日益明晰:读书使人充实,阅读塑造灵魂,阅读传递真善美。阅读使人类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阅读让人类眼界大开,拥抱世界。
阅读让我们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阅读让我们读懂自己,读懂人生,读懂祖国……
阅读之乐犹如巴金《海上日出》中的描写,“这时候,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就是图书馆。
世界是一本书,祖国是一本书,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读懂这些书,绝非易事,需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生命。
因此,不朽的不是书,而是读书人。
在遭遇人生危机和面临世界风云突变之时,化解危机最终还要靠人类自己。读者万岁!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杨佳,《中国科学报》记者卜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