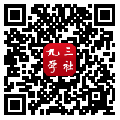人物小档案:李晓林,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系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九三学社社员,长期从事植物-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的研究。2009年开始,在河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农村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并探索专业硕士的新型培养模式。
“一咬牙就下去了”
人的一生总有几次重要选择。2009年,51岁的李晓林决定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将主要精力投向农业技术推广与专业硕士培养模式探索。此前,他已经在中国农业大学待了31年。1978年,他从唐山农村考入农大,从此离开农村。
为什么会重回农村?他说:“一个是为了学科的发展,一个是挑战自己。”李晓林从事植物“吃饭喝水”的植物营养研究。这是一门兼具基础与实用的学科。此前,李晓林一头扎进实验室,从事基础研究。“研究得很细”,他说,“但必须两条腿走路”。李晓林所在的资源与环境学院打算将“实用”这条腿也壮实起来。
从实验室到田间,李晓林坦言,“转型很难”。因为象牙塔的教学科研已经得心应手。“每年发几篇文章很容易,还能获得学校十几万元的奖励”。但农村却已陌生。“究竟能不能把庄稼种得比农民好,我心里没底”。种不好庄稼,对于大学教授来说难道不跌份儿吗?农村的苦能吃得了吗?
34岁破格晋升副教授;36岁破格晋升教授;38岁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过10多篇论文,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国家二级教授……这些厚重的成就会成为李晓林继续前进的负累吗?
李晓林决定突破自己。“在科研、教学方面已经做得不错,所以想挑战一下自己。”他觉得,没有什么输不起的,科研教学已经证明了自己。有人常常“刺激”他:“你们这学科对大生产没用。你们就发发文章,小瓶小罐,小打小闹。”心底那股不服气的劲儿被撩起,李晓林不信,平生所学只是空谈?“一咬牙就下去了。”达者兼济天下,知识分子也许永远无法割舍以所学报家国的使命感。
这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也是从象牙塔走向黄土地的回归。
科技小院开在农家门口
曲周,这是李晓林在农村的第一个据点。上世纪70年代,农大校长石元春曾多年在此主持改碱救灾,将以曲周为中心的72万亩盐碱滩变为米粮川。如今,解决了温饱的曲周农民,却面临增收难,水资源紧张、资源环境代价大的新难题。
李晓林最初的打算是,通过农技推广人员,把技术传授给农民。可土肥站负责人解释:“我们这没有几个人,也没车,走路骑车一天也看不了几块地。”李晓林感到,农村的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太大:“他们指望不上了,只能自己面对农民。”
李晓林在农大实验站南20公里处,找到了一大片小麦、玉米地,正好适合示范推广。李晓林想动员农民按照他们的指导种植,但有的农民不愿冒险,有的嫌麻烦,有的打心里就不服气: “我种了几十年的地,还不如你们?”看来,教授的头衔唬不了农民,只有拿出真本领,农民才信服。后来,李晓林常对驻村学生说: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没办法,只好通过乡、村两级干部动员,好说歹说,总算有20多户农民愿意拿出连片的163亩地来试验,建立核心示范区。有一家的地已种上棉花,现在要拔掉种植玉米。农户不同意。村干部来硬的,直接拔了。李晓林一方面感到基层干部不容易,一方面感到后怕:“没想到我们也做了恶人,万一他们上访怎么办?”
试验站离农民的试验田20多公里,中间还要穿过县城,拉货的大车常常造成拥堵。李晓林包了一辆面包车,一行5人早早起床,赶到试验田。那时已近夏季,为躲开中午的酷热,农民们很早就到地里,劳作到上午10点多回家。因此,李晓林的团队必须提前赶到,不然农民按自己的老把式来,试验就废了。
有时去晚了,村民已回家,李晓林他们只能在田间等着,因为下午不知道村民何时来。刚去的时候,农民并不把你当亲人。师生们被撂在地里,渴了,饿了,晒了,无人关心。李晓林只好派学生到县城买点饼干、矿泉水、方便面充饥,一个星期下来,肚子全坏了。

李晓林决定搬到示范区所在的白寨乡,队友们提出异议:“基地条件这么好,有房、有水、有电、有食堂。”这次,李晓林力排众议,他认为,住得离农民太远,工作无法开展。李晓林等请乡党委书记、乡长吃饭,请其帮忙解决房子。书记开起了玩笑:“李教授,这杯酒喝了就给间房。”李晓林极少喝酒,但这次为了房子,一扬脖,烈酒入肚,轰一下,觉得整个头就大了。 “也能喝嘛,再来一杯,再给一间。”李晓林豁出去了,又一杯下肚,头晕目眩。吃饭结束,李晓林一行担心书记说的是酒话,赶紧去要房子。乡长惊讶:“你们真要啊?”“真要”。房子原是司法所的,现在废弃不用了,一行人打开门一看,心凉了半截,院里长满了野草,没水,没厕所。但毕竟离农民近了。房子整好,一段时间后,李晓林觉得应该挂块牌子,方便农民好找。“这是个小院,我们是来送科技的,就叫科技小院吧。一查,网上没同名的,就是它了。”这个随口叫出的名字,后来成为响当当的品牌,农村的基层干部也成了好朋友,农业系统的人成了很好的合作伙伴。
千亩农田用上施肥机
渐渐地,村民与队友们熟了。见面打起了招呼。“你们怎么还没走啊?”“不走了,就住这儿了。”见真不走了,村民才慢慢愿意接近。所谓的“科技下乡”,农民见得多了,往往来几个人,看上一圈,栽个牌子就走了。李晓林笑道:“我们没有栽牌,却把人栽这儿了。”
感情上接近了,但要让农民信服还得拿出真本事。一场大风刮来了机会。
7月23日,一场大风刮倒了大面积的玉米,按以前,村民会将其扶正。农大师生与县农业局专家会诊后认为,这次倒伏在抽穗前,不会影响授粉,而玉米有能力自己恢复,人为扶正易造成茎部折断。李晓林立即组织师生,讲解其中科学道理。3天后,大部分玉米不扶而起,农民服了。
新技术往往要求农民投入更多精力,农民嫌累嫌麻烦,新技术虽好,却只能搁浅。农民给玉米追肥都采用撒播,这样肥料往往施不到位置,而且容易多施,浪费且污染环境。随李晓林驻扎曲周的首位研究生曹国鑫发现,虽然培训时,反复给农民讲过追肥一定要深施覆土,当时都说好,结果还是撒施。上去询问一位大姐,反而被噎了回来:“你说氮肥要深施,你给我拉小耧啊?”当地农民仍主要用小耧和更原始的铁锹深施肥。这两项技术均需两人配合,一天下来,前者可以完成2~3亩,后者可完成1~2亩,用小耧时必须有一位青壮年男劳力,但很多男劳力都外出打工了。一次,曹国鑫被在地头休息的一对夫妻拦下了:“大学生,有啥好法没有?这肥料往深了施吧,太费劲了,可是不往深了施,这肥料就浪费了。”曹国鑫脸上一阵滚烫:“我回去问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快速离开了。

李晓林听了直摇头:“这哪能行啊,走,到村里看看有没有追肥的机械,或能改装机械的能人。”师生二人在热心村民苏连春带领下一一上门询问村里的农机手,了解到,担心村民不愿意花钱请机器施肥,所以都没买追肥机。于是,师生二人邀请几位村民一同前往县城了解。转了好几家农机店,终于找到了全城唯一售卖这种机器的门店,大家都很高兴,在了解了机器的性能后,对使用机器的效益进行了分析。专家与老农围在一起算起账:每台机器1300元左右,每亩收费13元,汽油费4元,纯收入9元,每日追肥20亩,每天收入180元,7天就可收回成本,以后就是纯赚。“原来这机器不仅实用,还能赚钱,要不买一台回去试试。”几个农机手已心动。当场就有3位买了机器,当季就有300亩农田用上了追肥机,最后,产量也有较大提升。第二年,追肥机增加到10台,使用面积达到千亩以上,更多的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
10月,玉米收获,李晓林迎来了一场特别的考试:163亩试验大田究竟能增产多少?结果出来,增产幅度在16.7%左右,施肥量稍稍下降,农民劳作时间无增加。李晓林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科技小院成为农民常来的地方。
科技小院开枝散叶
临近的槐桥乡党委书记王晓伟听说科技小院搞的不错,找上门来:“李教授,派几个人到我们那边去吧,我们主要种苹果。”“苹果不会啊,我们主要是小麦、玉米。”“哪有不会的,就算不会,也比农民学得快吧。”没办法,李晓林只能应承了下来,将刘世昌、方杰两位学生送到该乡相公庄村。盛产西瓜的大河道乡也来“求救”, 当地西瓜套种在玉米、小麦中,但因为连作障碍,产量年年减少,李晓林把研究黄瓜的学生黄成东调来助阵。……
李晓林如同领军,在大生产的战场上调兵遣将。学生们不负器重,难题一个个被破解。

刘世昌、方杰从山东引进10万壁蜂为果树授粉,大大降低了歪果率;引进起垄覆草、反光膜着色等10项技术,提升了苹果产量质量。两位年轻人又发起苹果采摘节活动,让槐桥乡的苹果“红”了起来。黄成东、李宝深培育出西瓜嫁接苗,产量提高15%以上,提前上市10~20天,为破解连作障碍提供了解决办法。驻扎在第四疃镇王庄村的黄志坚开展技术服务将示范方的小麦产量提高18.3%,而被推选为该村党支部书记。打工潮兴起后,留守妇女成为劳动主力,李晓林通过女研究生建立“三八”科技小院,开办“三八”田间学校,学员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2013年50多人,学员的生产得以改进,生活更加丰富健康。有位学员原来喜打麻将,现在牌戒了,搞起了高产试验。空闲时,她们就在女研究生的带领下跳舞健身。
如今,科技小院延伸到南方诸省,延伸到企业,延伸到多个作物品种。李晓林的学生中,有的被派到广西隆安,为金穗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高香蕉技术服务;有的被到广东湛江提供芒果技术服务……
被问出来的专家
虽说是农大学生,但绝大部分从来没下过农村,有些连农作物还认不清。就这样,他们被放到农村。“这是真枪实弹啊,面对老百姓的问题,他们可以说不会,回去查清楚后再解答,但不能说不管,这就是逼着他们去学。”李晓林笑道:“这些学生成了我们探索培养农业专业研究生的‘小白鼠’。”
李晓林告诉每一位新来的学生:“要想待下去,就必须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然后再从农民变成一个研究人员。”
驻扎在大河道乡后老营村的李宝深有时会被问到病害、农药方面的问题,有的很专业,常常卡壳,只能说:“让我回去确定一下,再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好不好?”听到他们说“中”的时候,“我真有种得救了的感觉。”他回去后,问老师同学、农技员,查资料,哪怕不睡觉也要把问题搞清楚。
在科技小院待上一、两年,同学们从以前见到问题就想躲,变成了碰见问题就争着上;从一问就倒,成了百问不倒。这是被农民问出来的专家。
田间也可出论文
小院的新学生一般会在5、6月份到曲周,提前进入学习状态。到9月正式开学之前,李晓林要求每人至少写一篇文章:“只有文章是跟你一辈子的东西,也是能证明自己能力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没有这些,你跟农民没有区别。”这可难坏了同学们,大部分人从未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农业推广硕士也不要求发表论文,许多人根本就没想过发表论文。大家感到疑惑:不在实验室做实验,也能发表论文?
学生刘瑞丽接到任务后,就一脸愁相。李晓林给她支招。
“来曲周下地了吧?”
“玉米播种时去过。”
“有没有观察到地里有什么问题?”
“有,我跟师姐去司寨取样的时候发现有一块实验室旁边的花生缺铁特别严重。”
“把你看到花生缺铁的现象描述出来,再从文献中查查缺铁都有哪些防治办法,再根据植物营养的知识思考一下,针对曲周盐碱地的现状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解决办法?”
刘瑞丽的思路一下清晰起来,不久,“河北省曲周县花生缺铁原因分析及防治措施”初稿形成,经李晓林修改后,投给杂志,后被刊发。这也成为激励后来者的一个样本。
农地不仅盛产粮食,也盛产论文。曲周学生的论文发表数量之高超出了李晓林的预想,有位学生一年下来,发表论文10多篇。
学生们论文开题答辩也在曲周进行,除老师外,乡、村两级干部、农民都要参加,学生们的答辩,要让他们满意才行。他们唯一不满的是,答辩通过以后,学生们就要毕业离开。
“学生们比我行”
科技小院有个品牌叫冬季大培训,学生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给农民进行科技培训。说话都脸红的学生们克服了语言、心理、知识等方面的困难,成为农民的讲师。一年下来,每位学生平均要为农民培训30场次以上,做报告10余次,其表达能力、演讲水平,明显高于同龄研究生,而传统培养方式下的研究生锻炼的次数才一、两次。曹国鑫还荣获了北京市“党在百姓心中”宣讲活动优秀宣讲员一等奖。培训开始后,村子里看电影的人少了,参加培训的人越来越多。
李晓林要求每位学生每天都写工作日志,并发给自己及其他老师。“你写了吗?”成为了学生们见面时的最流行的问候语。曹国鑫是李晓林第一个驻扎在曲周的学生,“每天都写日志,这是我对曹国鑫的第一个考验,看他能不能在农村待得住。”有几天,曹国鑫中断了日志,远在巴西开会的老师发来邮件:“怎么一直都没有收到日志啊?要坚持写。”李晓林利用日志迫使学生们每天去总结,去提炼,日志见证着每一天的进步。如今,曹国鑫已经积累到800多期厚厚的日志。每位学生的日志都成为他们青春岁月的珍贵记忆。
在最难就业季,科技小院的学生们成了香馍馍,他们不是找工作,而是挑工作。有人在年薪12万与读博之间选择;有的还未毕业,已被预订。
作为老师,学生的成绩是李晓林最大的欣慰。他常笑言:“解决农民实际问题,学生们比我行。”中国农大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中心授予基地研究生们“科研与社会贡献特等奖”;时任曲周县委书记的申玉娥说:“课堂办到田间地头,大学生不仅自己收获了知识和能力,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也是实实在在的。”还有国外研究者来小院考察,对于这种农技推广与研究生培养方式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张于牧)